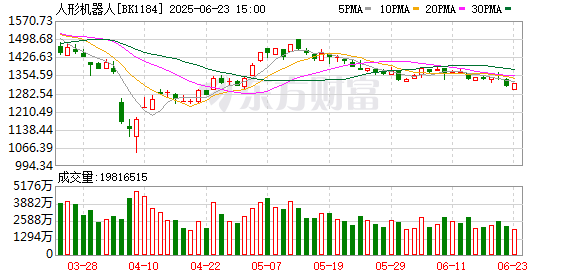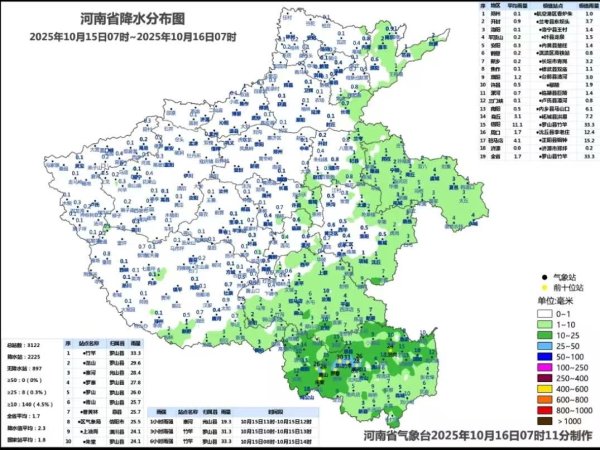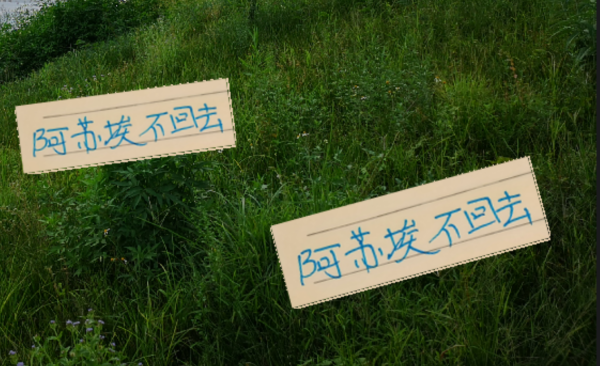1962年11月18日8时30分,我军部队集结完毕后与印军开始了在边境地区的第二阶段战役。战斗持续至11月19日下午的时候我军部队结束在邦迪拉阵地上的战斗万无优配,尽管当时我军大获全胜,但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1962年11月19日,在邦迪拉阵地上的后续战斗过程中,我军在32高地上损失惨重。在之前近一个月的作战中,我军还很少出现如此损失惨重的情况,32高地为何如此玄乎?难道印军当时还留有后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当时发生了什么。
在11月18日的战斗中,我军负责在邦迪拉主峰一带作战的第11师第33团3营大获全胜,占领了邦迪拉主峰一带的大部分印军阵地。能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战果,一方面是因为印军士气全无,稍作抵抗便全部溃逃;另一方面则是我军战斗力强悍。邦迪拉作战第一天就大获全胜,这让我军士气大涨,但很快意外就来了——我军不仅在32高地损失惨重,还牺牲了一位指挥官。
在1962年10月20日中印边境战争开始之前,印军就先后在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领土之上建立了43个武装据点,到了1962年6月之后,印军更是继续向我方藏南地区渗透,有的哨所已经修到了距离我军边防哨所几米的地方。所以当时在战斗中,我军的任务不仅仅是将进攻我们的印军打跑,还要将这些印军建立的武装据点拔掉。

在第一阶段的战役中,我军已将印军在我境内修建的大部分据点拔除或占领,在第二阶段的作战中只需要对残余的几个印军据点进行收尾性的精准拔除即可。
在这个过程中,我军第11师第33团的任务是拿下32高地,夺取西山口。32高地外围全是密密麻麻的印军地堡,但只有拿下这里,才能顺利占领西山口,进而削弱印军对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的控制,最终实现将印军赶至传统习惯线以南地区的目的。
在战斗开始之前,第33团的战士们都以为拿下32高地会像之前的战斗一样顺利,但这一次,33团遇到真正的挑战了,32高地怎么也攻不上去。
中印边境线全部都位于高原地区,32高地的海拔更高一些。驻守在这里的是印度陆军第11旅,驻扎兵力为1个营。32高地是印军第11旅纵深阵地的核心阵地,原先是预备在其一线阵地作战一旦失利后,依托其组织纵深防御继续进行顽抗的,所以该阵地的防御措施做的很不错,第11旅旅长席尔瓦称“它是万无一失的”。
在32高地以东地区是几个无名高地,印军第11旅的旅部就设在其后,东边是瓦弄机场。另外,32高地一带的地形也十分险恶,两侧均是悬崖深沟,印军还在必经道路口和进攻的绝佳位置埋设了地雷。因为环境限制,我军刚发动进攻时,印军在32高地两侧的火力点就向我军发动进攻,形成了交叉火力网,导致我军无法继续前进,各条战线上都陷入了胶着。
为改变战局,33团采取了多股部队多路出击的战术,但这样一来,人数优势在一人多宽的山路上就无法显现了。印军占领着32高地上的有利地形,易守难攻,让我军吃了不小的亏。

参战老兵谭书藏回忆:“32高地有个木堡,这个木堡是印军一个连队的指挥所,火力比较强,周围都打下来了,就是那个木堡打不下来。”
由于印军防守地堡的火力过于猛烈,我军部队无法前进,而32高地又是一个必须要快速拿下的地标万无优配,一次次冲击都被印军火力压制,牺牲的战士越来越多。
根据老兵谭书藏的回忆,我们可以大概还原当时第33团采取的进攻战术:正面派一部分部队进行火力掩护,只射击不冲锋,另派一部分队伍从侧翼发动进攻。
老兵谭书藏在回想战斗情景时表示:“我们正面没有发起冲锋,只进行火力掩护,就是3排牺牲了10个,负伤7个。当时我所在的部队的任务就是在正面进行火力掩护,眼看着侧面阵地的冲击多次都不成功,心急如焚。”
就在万分紧急之际,一位名叫陈代富的战士冲了上去。
老兵丁克云回忆:“32高地的山梁很陡,敌人机枪火力密集,人就根本上不去,几个战士都负伤牺牲了,陈代富主动请缨上去,他上去的时候在路上就负伤了,没想到过了一会儿他又起来了,又拿着爆破筒继续上,陈代富三滚两爬的爬到地堡顶上,地堡被炸开了一个缝,印度兵的工事不像国民党的工事是钢筋水泥的,他们的工事是用原始森林里的木料摞起来的,上面盖的土,把土一炸,就炸一个洞。”
前面冲锋的战士们不是倒在了地堡前,就是让爆破筒在地堡外爆炸,尽管没有完成爆破地堡的任务,但经过几轮的冲击,终于还是把地堡炸出了缝隙。此时陈代富明白,想要拔掉这个地堡,就必须将爆破筒伸入地堡中爆炸才能达到效果。

老兵刘家丰回忆:陈代富冲上去后,就从地堡顶部往下插爆破筒,因为其他地方没有缝隙了,插好爆破筒拉完火后,陈代富就准备离开,但敌人又推出来了。印军当时没有装备这样的武器,不认识这是什么,但他们知道肯定不是好东西,就使劲往上顶,陈代富插下去,他们往上顶,爆破筒的引爆时间只有7秒钟,陈代富一看不得了,又往下推。就在爆破筒即将爆炸时,班长向陈代富喊道:快下来。陈代富立马打两个滚从地堡顶部下来了,之后炸弹爆炸。
翻滚中的陈代富顺着这个爆炸的冲击力一直滚到一个洼地。地堡被炸后,战士们紧急冲上去收复32高地。
从老兵史悠俊的口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陈代富的情况,“冲锋的时候陈代富还埋在炸弹冲起的墟土里,埋了半截身子,后面我们赶快把他扒了出来。那个地堡不高,陈代富的枪就在身前,人是跪着的。跪着以后,整个腿就把枪眼给堵上了,所以我们抬的时候看见射击孔都是黑色的。”
受伤的陈代富鲜血染透了大半个身体,伤口一片血肉模糊,这情景令新兵史悠俊不忍直视。据史悠俊回忆,那天在32高地上的战斗一直到下午才结束,战斗结束后饭才送上来,“吃完饭以后我们又开始把牺牲士兵的尸体往回运。”
在这场32高地的攻坚战中,史悠俊所在的9连伤亡接近五分之一。
身为战场救护员的史悠俊负责战场救护,回忆道:“找伤员的时候咱们的战士没有一个哼哼的,所以你得认真找,要是他是哼哼、喊叫的话,你就知道他在哪,偏有人不,他不言语,而且你到他跟前还说先抬别人,他们就把枪往腿这儿一竖,子弹上膛说一旦印度兵来了,这枪一抬就可以打。”这就是我们的战士。
后经战斗统计,在32高地攻坚战中,我军共摧毁了印军构筑的42个地堡。且印军工事全部位于易守难攻的优势地位,目前我方并未公布具体的伤亡数据,但从这里就可以知道这场攻坚战的难度有多大。另外,在整个瓦弄战役中,第33团及配属友军部队共击毙、俘虏印军1250多人,33团作为其中的主力部队,在这其中的功劳并不小。
1963年初,解放军军报上曾经刊发过一篇名为《将红旗插向邦迪拉主峰》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就提到了33团在中印前线浴血奋战、攻克印军阵地邦迪拉主峰的故事,这也是我军在中印战争期间最后一次大规模的部队交火。
在这篇新闻报道中,记载了我军在战斗胜利一天之后突然遭遇的变故,当时我军损失惨重,在邦迪拉山脚下的遭遇战中还牺牲了一位营长,成为自中印边境战争开始后我军烈士中军衔最高的一位指挥官。
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竟让我军在短短两天时间内如此落差。我们根据第11师33团老兵的回忆,可以大概将当时的战斗情况进行还原。
1962年11月19日,孙维吼所在的第33团3营9连接到命令堵住被困印军的突围方向,当他们赶到指定作战位置的时候正好碰到了印军,战斗一触即发。
这场遭遇战打得非常激烈,印军已经穷途末路,所以我们面对的敌人比之前的任何一场战斗都要凶狠,他们疯狂扣动扳机,子弹和炮弹接连不断的落在我军阵地上。

孙维吼回忆:“我前面都是烟、火光,耳朵里听到的全是爆炸声,敌人进攻猛烈的时候只能在工事内躲避,你趴在那儿,你也不可能抬起身子到处看,你这个视线只有你的前面,看那儿有车着火。”也正是在躲避敌人猛烈射击的时候,孙维吼突然看到营长中弹牺牲了。33团3营营长李白石向来是作战最勇猛的,在当天的战斗中也是冲在最前面带领战士们向印军发动进攻,但战斗还未结束,营长便中弹牺牲了。
眼看着先前还活生生的战友瞬间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这对孙维吼的打击很大,但很快,他内心的恐惧就和战友们一样,逐渐变成怒火升腾了起来,我军向印军发动猛烈反击。关于后续反击的具体情况,孙维吼在回忆的时候是这样形容的:“大家非常气愤,都要为营长报仇,由于我军部队的火力比印军强,重机枪轻机枪都有,在一瞬间,我军的子弹就像下雨一般朝着印军阵地盖过去了”。
在我军强大的火力压制下,印军很快就被消灭殆尽。在此次战斗中,我军第11师第33团第3营以牺牲、受伤76人的代价,击毙印军170人,俘虏印军30多人。
在老兵孙维吼创作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六十年人生回顾》中,他是这样形容当年那场战役的:从军18年,邦迪拉山脚下的遭遇战至今仍留在记忆最深处。
不仅是他们不会忘记当年的战斗生涯,如今生在和平年代的我们,也不会忘记先辈用鲜血换来的美好生活!
天创网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